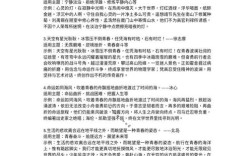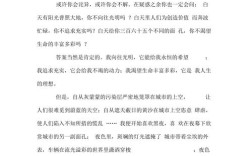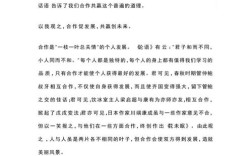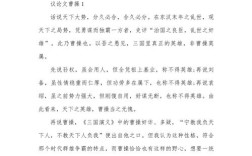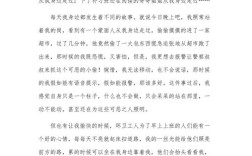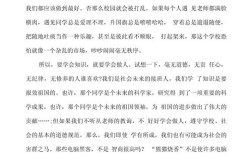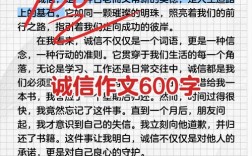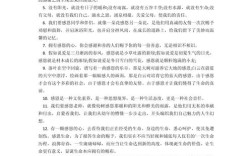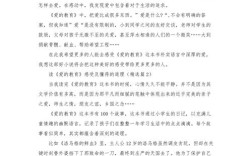于“无用”处,窥见大用
在当今这个高速运转、效率至上的时代,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界限似乎被前所未有的清晰划分,我们追求速成的技能,追捧热门的学科,渴望每一分投入都能立竿见影地兑换成可见的价值——财富、地位、名望,在这样一股“实用主义”的洪流中,“无用”之物,仿佛成了被时代洪流冲刷至岸边的孤石,显得格格不入,甚至有些可笑,当我们拨开功利主义的迷雾,向“无用”的深处探寻时,便会惊觉,那些看似无用的存在,恰恰蕴藏着滋养生命、塑造文明、启迪未来的“大用”。
“无用之用”首先在于涵养精神,构筑个体生命的深度与广度。

人生的价值,远不止于谋生工具的积累,一个人的精神世界,如同一片需要精心打理的花园,若只种满能立即开花结果的功利之树,这片花园终将单调、脆弱,而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阅读,一本与专业无关的哲学著作,一首晦涩难懂的诗,一段无关紧要的历史,便如同花园里的青苔、野花与溪流,它们不能直接兑换成金钱,却能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,丰富我们的情感体验,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,正是这些“无用”的滋养,让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复杂与无常时,拥有更通达的智慧与更从容的心态,苏轼一生宦海沉浮,屡遭贬谪,若只从“仕途”这一“有用”标准衡量,他无疑是“无用”的,正是这“无用”的流放岁月,让他寄情山水,醉心书画,创作出《赤壁赋》等千古名篇,其精神境界之高远,人格魅力之伟大,远超任何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”,他的“无用”,成就了他人格的“大用”。
“无用之用”其次在于孕育文明,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。
回望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,那些颠覆性的创造与进步,往往并非源于对“有用”的刻意追求,而是诞生于对“无用”的好奇与探索,古希腊人研究几何学,纯粹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和谐与秩序,在当时看来,这些抽象的线条与公理毫无“实用”价值,正是这门“无用”的学问,奠定了西方科学精神的基石,最终催生了牛顿力学、相对论等改变世界的理论,达·芬奇传世名作《蒙娜丽莎》的微笑,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,但他同时所做的无数“无用”笔记——关于飞行器、人体解剖、水利工程的奇思妙想——在当时看来更是天马行空,不切实际,但这些“无用”的探索,却闪耀着跨学科、前瞻性的智慧光芒,预示了现代科技的诸多方向,历史反复证明,科学的疆域、艺术的边界、文化的深度,正是在对“无用”的宽容与鼓励中,才得以不断拓展,倘若社会只推崇立竿见影的“有用”,那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科技与文明,或许将永远停留在萌芽状态。
“无用之用”更在于守护人性,维系社会的温度与韧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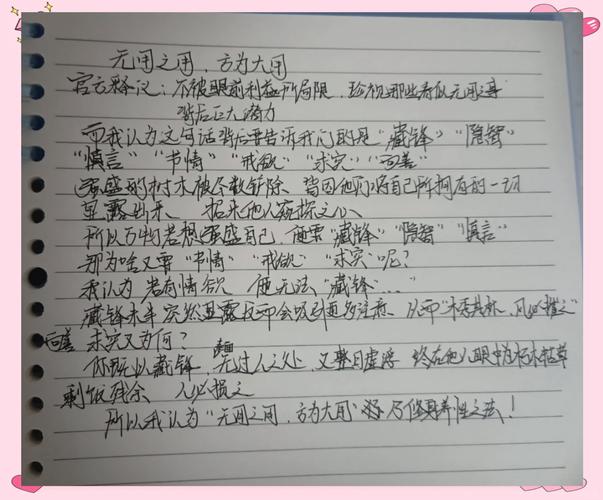
一个健康的社会,不应是一台冰冷的、只追求效率的机器,它需要那些“无用”的角落来安放人性中最柔软、最温暖的情感,街角的公园,不能产生GDP,却是市民休憩、交流、感受自然的场所;社区的图书馆,不能直接创造利润,却是知识传播、启迪民智的殿堂;免费的博物馆,不能带来经济回报,却是连接历史与未来、传承民族记忆的纽带,这些“无用”的公共空间与事业,如同社会的毛细血管,输送着关爱、信任与归属感,让社会这个有机体充满活力与温度,当我们将目光从宏大的经济指标转向个体的幸福感时,便会发现,正是这些“无用”的美好,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与尊严。
诚然,我们并非要全盘否定“有用”的价值,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,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,是安身立命之本,我们警惕的,是那种将“有用”作为唯一标尺,从而将“无用”彻底驱逐出我们生活与视野的极端功利主义,这种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,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扁平,让我们的文明变得浅薄,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冷漠。
让我们学会与“无用”和解,甚至拥抱“无用”,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不妨留出一点时间,去读一本“无用”的书,去欣赏一段“无用”的音乐,去进行一次“无用”的远足,让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规划中,为那些“无用”的科学与艺术、文化与公益留下一片空间,因为,真正的“大用”,往往就潜藏在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等待与探索之中,它不喧嚣,不张扬,却如空气与水一般,默默滋养着我们,让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人,也让世界成为更值得留恋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