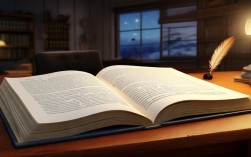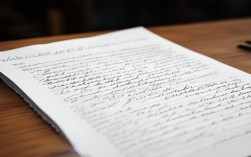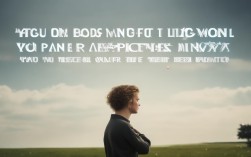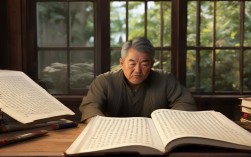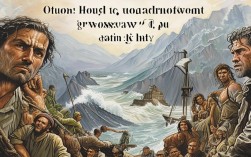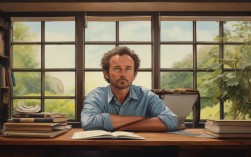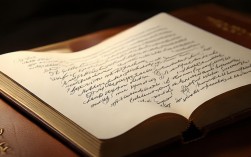景由心生,境由意造——论写景的深层意蕴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初读此句,我们无不为其壮阔的景象所震撼,当我们拨开这如画的景致,便会发现,王勃笔下的不仅仅是晚秋的江景,更是他怀才不遇的孤高与“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”的深沉感慨,写景,从来都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机械复制,它是一场“景由心生,境由意造”的精神创造,真正的写景,是景、情、理的交融,是作者内心世界投射于外物,又赋予外物以灵魂的艺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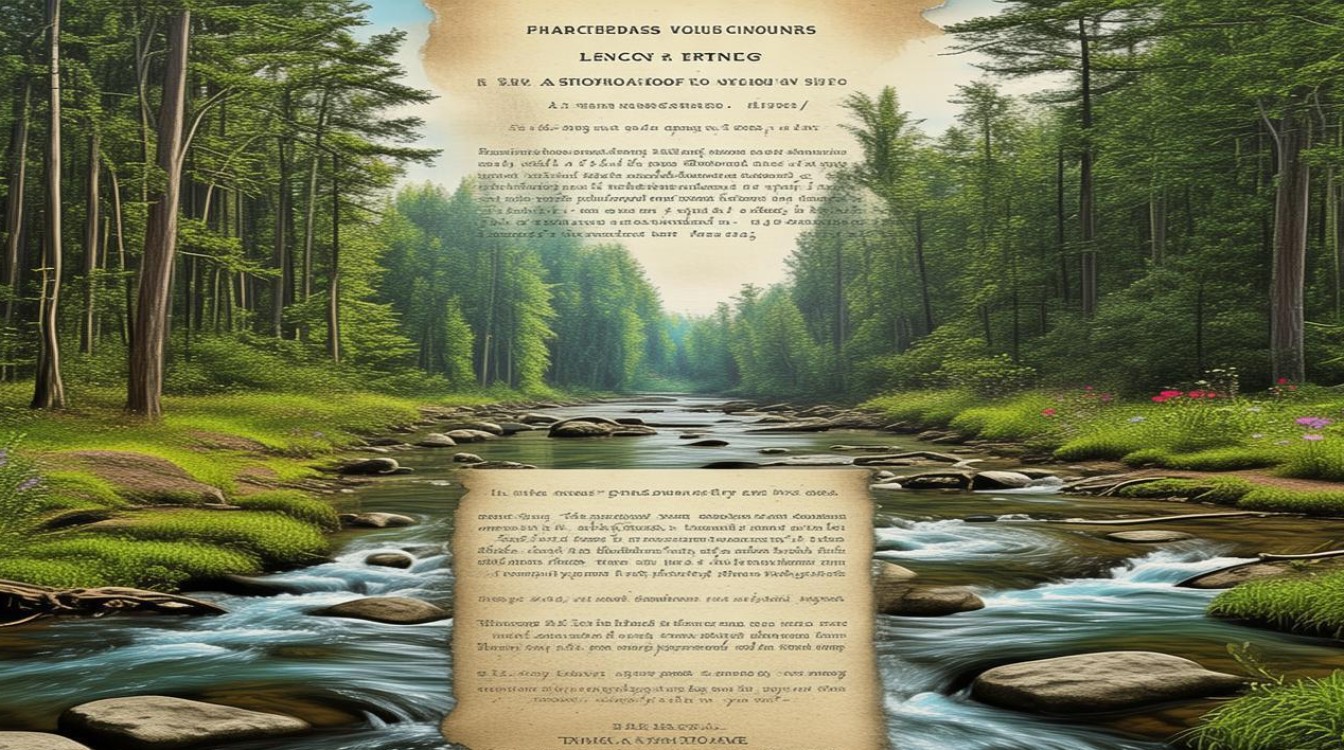
写景,是情感的载体,是作者心迹的“心电图”。
中国古典文学素有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之说,景,是作者情感的外化,是内心波澜的具象化表达,同样是写月,李白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月是清冷的,是游子思乡的愁绪化身;苏轼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月是温润的,是超越时空的美好祝愿;而张若虚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”,月则成了永恒与短暂的哲思见证,景本身并无悲喜,是作者将自己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融入其中,才使得寻常的山水、日月、花鸟,都染上了独特的情感色彩,优秀的写景作品,我们总能透过文字,触摸到作者那颗跳动的心,无论是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中“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”的孤寂,还是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博大,其景其情,早已水乳交融,不可分割,写景,正是这样一条通往作者内心深幽处的幽径。
写景,是哲思的熔炉,是生命感悟的“启示录”。
更高层次的写景,不止于抒发一时一地的情感,更在于借景说理,托物言志,它将自然界的物象作为哲思的起点,通过精妙的比喻、象征或对比,引出对生命、宇宙、社会的深刻洞见,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,面对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的江景,由“哀吾生之须臾”的悲,转向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”的悟,最终在“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哲思中获得超脱,他笔下的江风、明月、水波,都成了承载其生命智慧的载体,再看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,潭水的“清澈”映照了作者被贬谪后内心的澄澈与孤高,潭石的“岸势犬牙差互”则暗示了仕途的险恶与环境的险峻,景不再是单纯的背景,它本身就是一种哲理,一种象征,是作者在困境中与世界的对话,是其生命体验的结晶,这样的写景,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美的享受,更是思想的启迪。
写景,是艺术的创造,是“眼中之景”与“心中之景”的升华。
“艺术源于生活,但高于生活。”写景正是如此,它始于对客观景物的观察(眼中之景),但绝不止于此,作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想象、情感与思想,对眼前的景物进行筛选、重组与再造,最终创造出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艺术境界(心中之景),王维的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,正是这种艺术创造力的极致体现,他笔下的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不是对雨后山林的简单拍照,而是经过诗人宁静心境过滤后的景象,充满了禅意与画意,同样,画家笔下“留白”的艺术,看似是景物的缺失,实则是给观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,是“以无胜有”的更高层次的写景,这种创造,需要作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、深厚的情感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,它让写景从一种记录行为,升华为一种艺术再创造。
写景绝非简单的描摹,它是一条连接内心与世界的桥梁,是情感流淌的河床,是哲思绽放的土壤,更是艺术升华的熔炉,优秀的写景作品,总能让我们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,感受到作者的生命温度与思想深度,它告诉我们,世间万物,唯有被“心”所照见,被“意”所塑造,才能真正拥有不朽的生命力与艺术价值,作为写作者,我们当学会用心去感受,用情去书写,让我们的笔下的每一处景,都成为我们独特灵魂的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