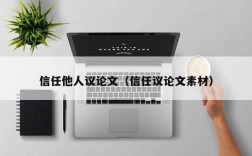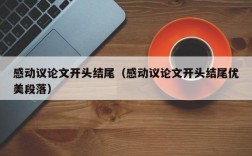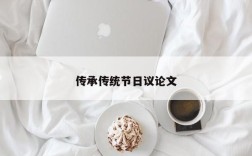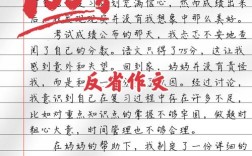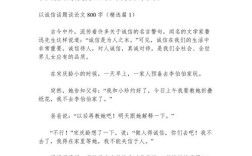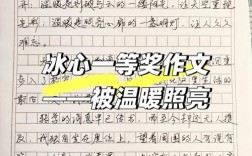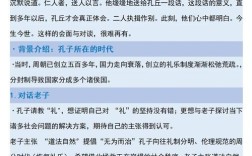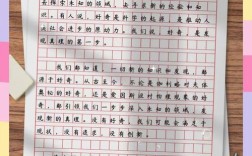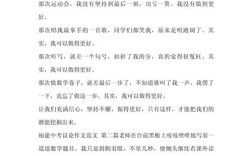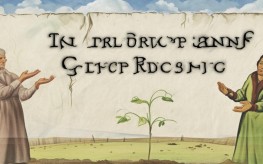驯服“熊孩子”,更要“驯服”背后的“熊大人”
在公共场合,你是否曾被尖叫奔跑的孩子惊扰了观影的雅兴?在安静的图书馆,你是否曾被旁若无人的嬉闹声打破了片刻的宁静?在网络上,那些毁坏他人财物、毫无敬畏之心的“熊孩子”视频,总能瞬间点燃公众的怒火,这些被称为“熊孩子”的特殊群体,正以其惊人的破坏力和挑战社会规则的姿态,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公共议题,当我们急于给这些孩子贴上标签、口诛笔伐时,是否更应该冷静思考:是谁,将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孩童,变成了人人喊打的“熊孩子”?问题的根源,往往不在于孩子本身,而在于那些本应引导他们、却选择纵容甚至“作恶”的“熊大人”。

“熊孩子”的横行,是家庭教育的严重失职。 孩子如同一张白纸,他们的行为模式、价值观念,无一不是家庭环境和社会教育的投射,所谓“熊孩子”,本质上是对规则的无知与漠视,这种无知,源于父母教育的缺位,许多家长秉持着“孩子还小,不懂事”的“护犊”心态,对孩子的无理取闹、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视而不见,甚至美其名曰“天真活泼”,当孩子在餐厅里追逐打闹,父母笑着说“孩子精力旺盛”;当孩子撕毁他人的书籍,父母一句“他还是个孩子,跟你道个歉就行了”便想息事宁人,这种“无限宽容”的溺爱,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学习规则、承担责任的机会,它向孩子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:世界会围绕我旋转,规则是为别人设立的,我的行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,在这样的“无菌”环境中成长,孩子自然无法形成健全的是非观和同理心,最终演变为令人头疼的“熊孩子”。
“熊孩子”的泛滥,是社会公德意识的集体滑坡。 个体的“熊”是家庭问题,而群体的“熊”则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弊病,当一个社会对“熊孩子”的容忍度越来越高,对失职父母的谴责声越来越弱时,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德失范的表现,公共场所的规则、他人的合法权益,在“自家孩子”的利益面前变得无足轻重,这种“以我为主”的利己主义心态,正在侵蚀着社会的公共空间,我们常常看到,在地铁、飞机等密闭空间里,孩子的哭闹声成了全车人的“背景音”,却鲜有家长主动采取措施安抚,反而觉得是别人“事多”,这种将个人便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行为,不仅破坏了公共秩序,更在潜移默化中教会孩子: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,他人的感受是可以被忽略的,当这种心态成为常态,社会便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尊重。
根治“熊孩子”顽疾,需要多方合力,标本兼治。 简单的指责和谩骂,无异于隔靴搔痒,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,要真正“驯服”这些“小野兽”,必须从根源入手,构建一套完整的“驯服”体系。
家长必须承担起首要责任,成为孩子的“第一任规则导师”。 这并非要求父母对孩子严苛以待,而是要做到“严慈相济”,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与陪伴;必须在原则问题上“寸步不让”,要明确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,什么不可以做,并为他们的行为设立清晰的边界,当孩子犯错时,要引导他们认识错误、承担责任,而不是一味袒护,真正的爱,不是无底线的纵容,而是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、受人尊重的人。
社会应建立更明确的“规则共识”与“惩戒机制”。 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应敢于对不文明行为说“不”,建立明确的儿童行为规范,并在必要时提醒甚至制止家长的失职行为,法律层面也应有所作为,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“熊孩子”行为,其监护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,只有让“熊大人”们明白,纵容孩子是有代价的,他们才能真正警醒起来,履行好监护职责。
学校教育应强化公德与法治精神的培养。 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殿堂,更是塑造品格的熔炉,应将社会公德、规则意识、法治观念等融入日常教学,通过主题班会、社会实践等形式,让孩子从小就懂得尊重、理解和敬畏,明白权利与义务是并存的。
“熊孩子”现象是一面镜子,照出的不仅是孩子的顽劣,更是背后“熊大人”的失职、社会公德的模糊,我们不应将所有的矛头指向那些尚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孩童,而应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教育与社会问题,唯有当每一位家长都能负起责任,当社会能坚守规则底线,当教育能播撒下尊重的种子,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驯服“熊孩子”,也才能共同营造一个更加文明、和谐的社会环境,毕竟,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孩子,明天社会就会如何对待我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