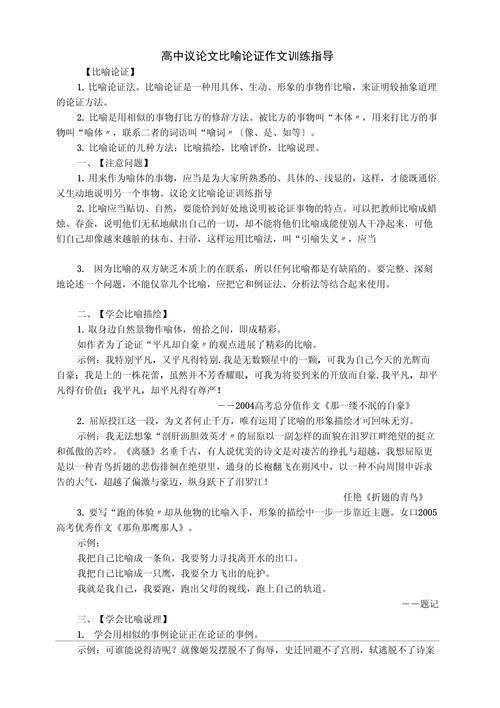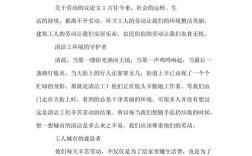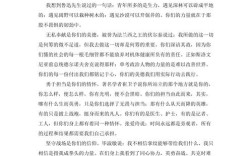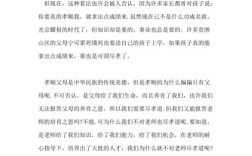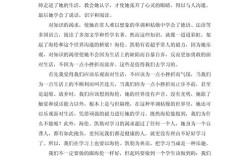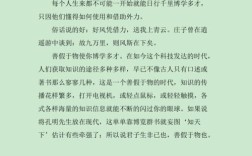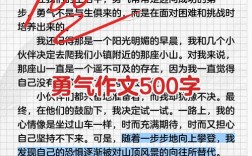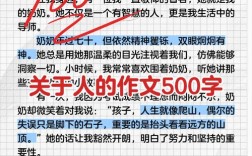固执,在多数语境下被视作贬义词,常与“顽固”“偏执”挂钩,仿佛一个人若沾染了“固执”的标签,便意味着不可理喻、不懂变通,若剥离情绪化的偏见,从认知与行为的角度审视,“固执”的本质其实是“对自我认知的坚守”,这种坚守并非全然负面,它既可能是阻碍成长的枷锁,也可能是成就事业的基石,关键在于,我们所坚守的是“认知”本身,还是认知背后的“真理”;是僵化的“,还是动态的“探索逻辑”。
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,固执的本质是“认知闭合需求”的极端体现,所谓认知闭合,指个体在面对模糊、不确定的信息时,产生的一种“渴望获得明确答案、结束混乱状态”的心理动机,适度认知闭合能帮助人快速决策、避免内耗,比如科学家在实验中提出假设后,会通过反复验证来“闭合”认知;医生面对复杂病例时,会凭借经验初步诊断后逐步调整方案,但若认知闭合需求过强,便会演变为“拒绝接受新信息、捍卫既有结论”的固执——此时的“坚守”已脱离对真理的追求,沦为对“自我正确性”的心理防御,就像一位坚持“地心说”的学者,即便面对望远镜中的星体证据,仍用“本轮均轮”理论强行解释,看似在捍卫真理,实则是在维护“我没错”的认知安全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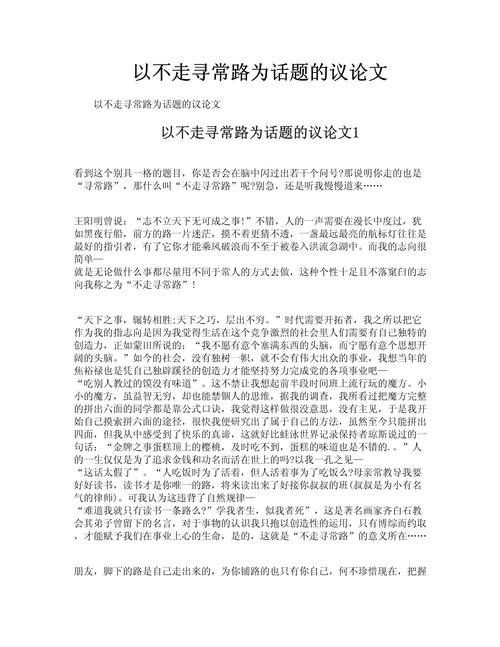
固执的价值,往往体现在对“核心原则”的坚守上,真正的固执,不是对细枝末节的偏执,而是对底层逻辑的笃定,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过程,便是对“中医药宝库”这一核心认知的固执坚守,当西医普遍化学合成药物时,她却坚信古籍中“青蒿一握,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”的记载蕴含着科学真理,即便在提取屡次失败后,仍坚持低温萃取的思路,最终突破难关,这种固执,不是盲目排斥现代方法,而是基于对“传统智慧可验证”这一信念的执着,最终推动了医学进步,同样,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,扎根大漠五十七载,面对“旅游开发”与“文物保护”的争议,始终固执地坚持“保护第一”的原则,用数字化技术让敦煌艺术“永生”,她的固执,是对文化传承使命的坚守,这种坚守无关固执与否,而关乎“什么更重要”的价值排序。
多数时候,我们所说的“固执”指向的是“认知僵化”——即拒绝更新认知模型,将阶段性结论视为永恒真理,心理学中的“证实性偏见”便是其典型表现: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,忽略或排斥矛盾证据,比如企业经营者若固执地认为“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”,便可能对市场变化视而不见,最终被时代淘汰;个人若固执地认为“我天生不适合学英语”,便可能拒绝尝试新方法,陷入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,这种固执的本质,是将“认知”与“自我价值”绑定——承认认知错误,仿佛就等于承认“我无能”,人们宁愿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,也不愿停下脚步重新审视方向。
如何区分“有益的坚守”与“有害的固执”?关键在于是否保持“认知的开放性”,有益的坚守,如同航船的锚,能让船只在风浪中保持稳定,但锚链始终留有余地,可根据洋流调整方向;有害的固执,则是将船焊死在礁石上,即便潮水上涨、船只倾覆,仍高喊“这是唯一的港湾”,具体而言,可从三个维度判断:其一,是否愿意主动接触“对立信息”?真正的认知笃定者,会主动挑战自己的观点,以检验其坚固性;而认知僵化者,则会主动屏蔽异见,构建信息茧房,其二,是否区分“事实”与“观点”?固执的人常将“我认为”等同于“事实是”,而理性坚守者会明确“这是基于当前证据的推断,若有新证据,我愿意修正”,其三,是否关注“结果反馈”?若坚守的行为持续带来负面结果,仍拒绝调整,便是固执;若根据反馈灵活优化策略,则是智慧。
在信息爆炸、快速变化的今天,我们更需要培养“动态的固执”——既不轻易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核心认知,也不对新信息、新方法抱有偏见,就像科学家波普尔所说,“科学进步的规律不是‘证实’,而是‘证伪’”,真正的认知成长,不是从“固执”走向“圆滑”,而是从“盲目的固执”走向“理性的坚守”:坚守对真理的追求,但不固守对真理的认知方式;坚守对价值的信仰,但不拒绝价值的时代表达,固执才能从贬义词,蜕变为一种可贵的品质——一种在喧嚣中保持清醒,在质疑中坚定前行的力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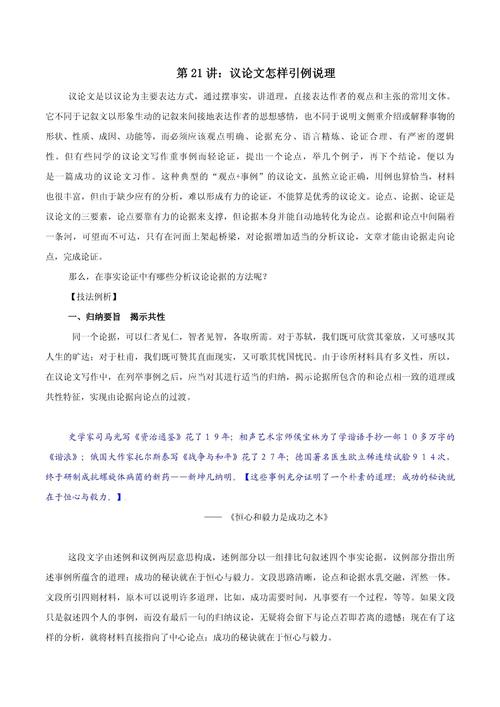
相关问答FAQs
Q1:如何判断自己是“坚守”还是“固执”?
A1:可通过“三问法”自我检视:一问“我是否在主动寻找反对我观点的证据?”若答案是肯定的,更多是坚守;若总在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,则可能是固执,二问“我的结论是基于当前所有信息,还是只符合我的偏好?”若愿意根据新信息调整,是坚守;若只选择符合既有结论的信息,是固执,三问“若坚持当前做法会导致严重后果,我是否愿意改变?”若能理性评估后果并调整,是坚守;若即便后果严重仍拒绝改变,是固执。
Q2:如何避免陷入有害的固执?
A2:培养“元认知能力”,即跳出自身视角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,比如定期反思“我为什么会这么想?有没有其他可能性?”建立“反馈机制”,将行动结果与预期目标对比,若长期偏离,及时调整策略;主动接触“异质信息”,比如阅读不同观点的书籍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流,打破信息茧房,避免认知单一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