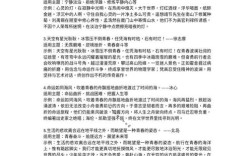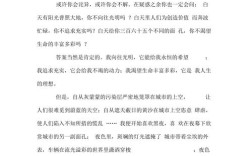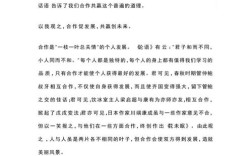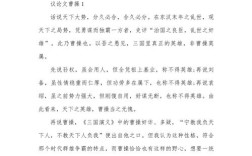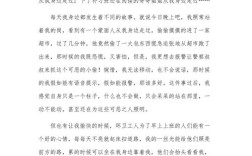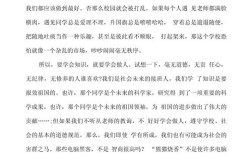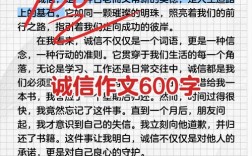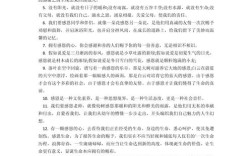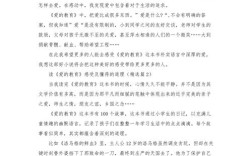悲剧:于毁灭中窥见崇高
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,悲剧始终是一面独特的棱镜,它折射出人性最深邃的幽暗与最璀璨的光辉,从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,从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,悲剧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,它以毁灭性的结局,迫使我们将目光投向生命的本质,追问命运的价值,悲剧并非单纯的痛苦宣泄,它更是一种净化、一种升华,一种在毁灭中窥见人性崇高的深刻艺术。

悲剧的核心,在于“毁灭”与“崇高”的交织。 它所呈现的,并非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烦恼,而是个体与强大、不可抗拒的力量之间的终极冲突,这种力量,可以是命运的无情、社会的桎梏、人性的弱点,也可以是人物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与执念,俄狄浦斯王越是竭力逃避“杀父娶母”的神谕,就越是在命运的棋盘上精准落子,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;哈姆雷特在理性的深渊中反复求索,最终却被复仇的烈火吞噬,他们的毁灭,是必然的,是宿命的悲剧,正是这种无可挽回的“毁灭”,才反衬出主人公在面对毁灭时所展现出的精神力量,俄狄浦斯在刺瞎双眼、自我放逐后,以其残缺之躯承担了命运的惩罚,展现了人类在绝境中尊严的完整;哈姆雷特“生存还是毁灭”的千古一问,则揭示了人类在行动与思考间的永恒挣扎,这种在毁灭面前不屈的抗争、清醒的认知和沉重的责任感,便是悲剧的“崇高”所在,它告诉我们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其长度,而在于其深度与高度。
悲剧的功能,在于“净化”与“反思”。 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提出,悲剧通过“卡塔西斯”(Catharsis)——即情感的宣泄与净化——使观众在恐惧与怜悯中获得心灵的涤荡,当我们为英雄的陨落而心碎,为不公的命运而悲愤时,我们并非沉溺于消极情绪,相反,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,将我们从日常的麻木中唤醒,让我们更深刻地共情他人的苦难,更敏锐地审视自身与社会的弊病,鲁迅先生弃医从文,正是因为他认识到,精神上的“悲剧”比肉体上的病痛更可怕,他笔下的阿Q,其“精神胜利法”是一种国民性的悲剧,鲁迅以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笔触,刺痛了国人的灵魂,促使整个民族进行痛苦的反思与自省,在今天,我们依然需要悲剧精神,当社会不公、环境危机、人性异化等现代性悲剧上演时,悲剧艺术提醒我们,不能视而不见,更不能麻木不仁,它激发我们的道德感与责任感,推动我们去改变、去抗争,从而避免现实中的悲剧重演。
悲剧的价值,在于赋予“有限”生命以“无限”意义。 人生苦短,世事无常,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命题,悲剧直面这一现实,它不提供廉价的安慰或虚假的希望,而是承认并展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,它也正是在这承认之中,找到了对抗虚无的力量,英雄的肉体虽会消亡,但他们为理想、为尊严、为爱所付出的努力,他们的精神与品格,却超越了时间的限制,化为不朽的丰碑,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,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,每日忍受鹰鹫啄食之苦,但他从未屈服,他的悲剧,彰显了为人类福祉而牺牲的伟大精神,这种精神,如同一座灯塔,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,让他们在有限的生命里,去追求无限的价值,悲剧告诉我们,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苦难,而在于如何赋予苦难以意义;不在于能否战胜命运,而在于是否敢于正视命运。
悲剧绝非“唱衰”人生的艺术,而是一剂苦口的良药,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,它以毁灭的残酷,反衬出人性的光辉;以情感的冲击,唤醒了沉睡的良知;以对生命有限性的正视,激发了我们对无限意义的追寻,在喧嚣与浮躁的时代,我们或许更需要悲剧精神,它让我们学会敬畏,学会同情,学会反思,更让我们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能够热爱生活,并以一种更坚韧、更深刻的方式,去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“崇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