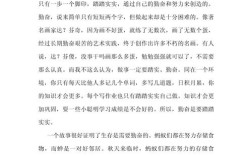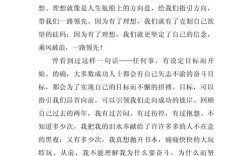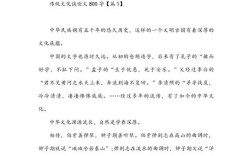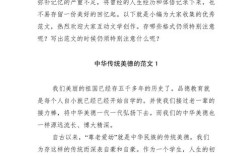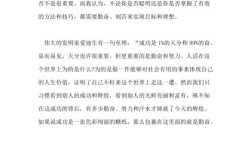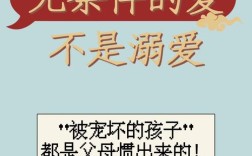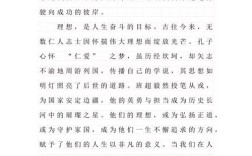谪仙入世,酒中狂歌——论李白诗歌中的矛盾与永恒
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星空中,李白无疑是最璀璨、最耀眼的星辰之一,他被冠以“诗仙”之名,其诗歌如天马行空,飘逸洒脱,仿佛不食人间烟火,当我们拨开那层浪漫主义与仙气的外衣,深入其诗歌的肌理,便会发现一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灵魂,他既是“谪仙人”,又是入世的儒者;既是酒中狂客,又是孤独的行者,正是这些深刻的矛盾,共同铸就了李白诗歌不朽的艺术魅力与永恒的生命力。
其一,是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矛盾碰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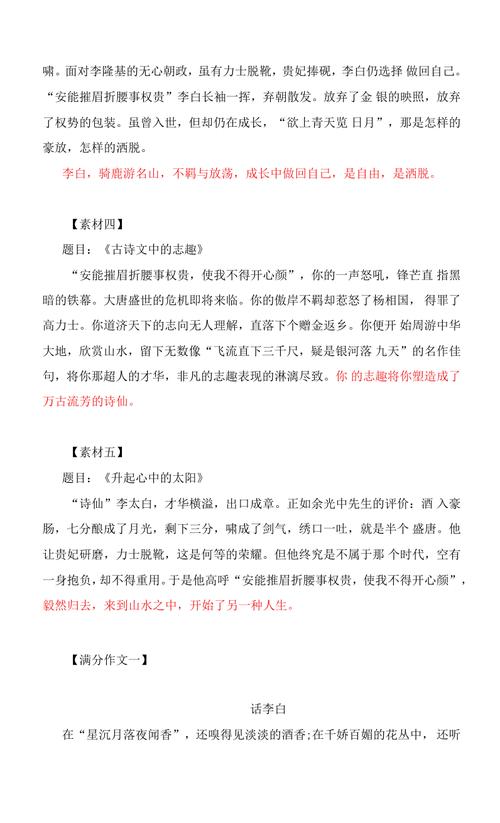
李白的一生,是“功成身退,济苍生”的政治理想与“且放白鹿青崖间”的逍遥精神交织的一生,他自比大鹏,渴望“扶摇直上九万里”,实现“申管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”的抱负,这种强烈的入世情怀,在他的《上李邕》中展露无遗: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,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溟水。”字里行间充满了睥睨天下的豪情与建功立业的渴望,他骨子里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,向往着绝对的精神自由,他“五岳寻仙不辞远,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将山水自然视为精神的归宿。
这种矛盾贯穿其始终,当他仕途顺遂,供奉翰林时,他高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,意气风发;而当他在政治上遭受挫折,被“赐金放还”后,他又能迅速转向,在山水与美酒中寻找慰藉,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,他的诗歌,正是在这种“入世”的执着与“出世”的洒脱之间反复摆荡,时而慷慨激昂,时而放浪形骸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,这种张力,让他既不是完全避世的隐士,也不是汲汲于名利的俗吏,而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间痛苦求索的伟大诗人。
其二,是“狂放不羁”与“孤独感伤”的内在统一。
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杜甫的这首诗,几乎成了李白狂放不羁形象的定论,的确,李白的诗酒人生充满了豪情与傲骨。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是他自信的宣言;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是他尊严的底线,他活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,用最纯粹的眼光看待世界,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情感,这种“狂”是对世俗规则的有力反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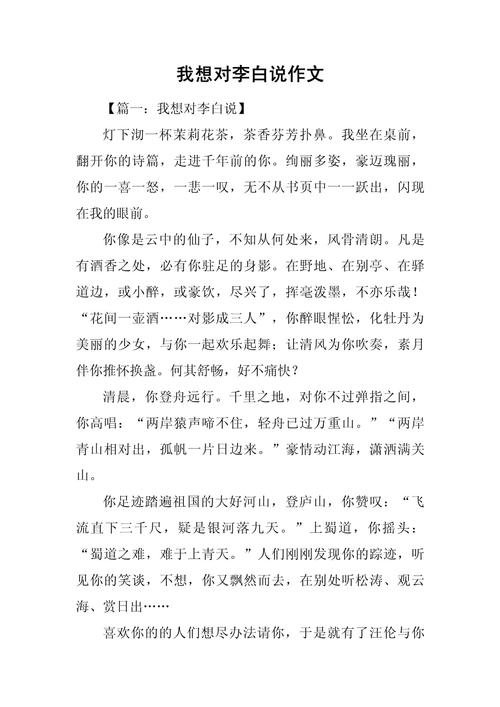
在这层狂放的外衣下,包裹的却是一颗无比孤独与感伤的心,他的孤独,是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的宇宙级的孤独;是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的无人理解的孤独;更是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的无法排遣的孤独,他的豪情万丈,恰恰是为了掩盖内心的失意与悲凉,他越是渴望被理解,就越是感到孤独;他越是狂放,就越是凸显出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,这种孤独感,并非消极的颓废,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,它让李白的诗歌在飞扬的想象之外,更添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与悲悯的情怀,使其狂放不羁有了情感的根基,使其感伤孤独有了超越性的诗意。
其三,是“盛唐气象”的巅峰代表与永恒的精神象征。
李白生于盛唐,长于盛唐,他的诗歌是盛唐精神最完美的注脚,盛唐的自信、开放、昂扬与进取,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,无论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雄浑壮阔,还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奇绝想象,都展现了那个时代恢弘的气魄与蓬勃的生命力,他笔下的世界,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光明希望的世界,这便是“盛唐气象”。
李白的伟大之处在于,他不仅属于盛唐,更属于所有时代,当安史之乱的惊雷击碎了盛唐的繁华,李白的人生也迎来了转折,他的诗歌也随之染上了一抹悲剧的色彩,但这份悲剧性却让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,他晚年的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中,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慨叹,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失意的抒发,而是上升为对人生终极困境的哲学思考,他所追求的绝对自由、独立人格与生命价值,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失意时的精神灯塔,他的人格魅力——“不屈己,不干人”,他对理想的执着,他对生命的热爱,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,成为一种文化符号,一个永恒的精神象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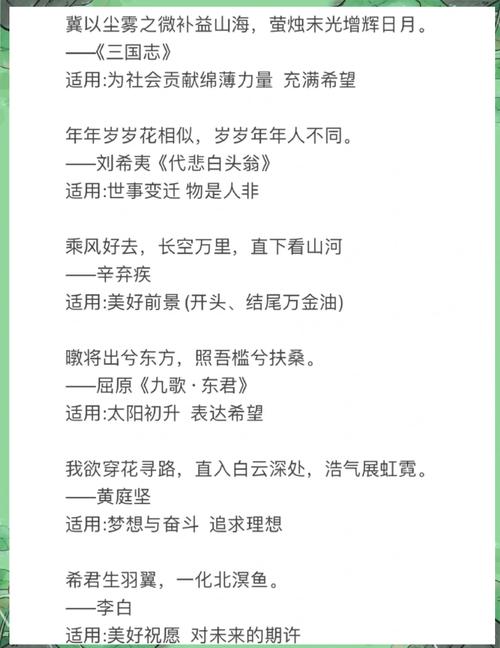
李白并非一个单一的、扁平的“谪仙人”,而是一个立体的、充满生命张力的复杂个体,他的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、“狂放”与“孤独”并非割裂,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成就,正是这些深刻的矛盾,让他的诗歌既有“黄河落天走东海”的气势,又有“白发三千丈”的愁绪;既有“手可摘星辰”的浪漫,又有“对此如何不泪垂”的悲悯,他用自己的生命与诗歌,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瑰丽的精神世界,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题,这谜题,正是李白千年之后依然能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,他,是盛唐的顶峰,也是穿越时空,永远与我们对话的谪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