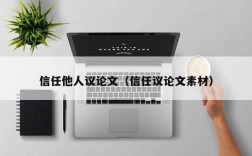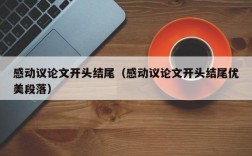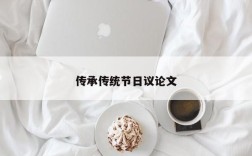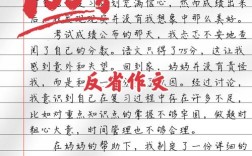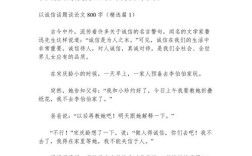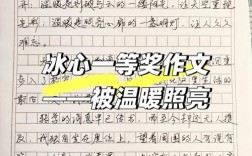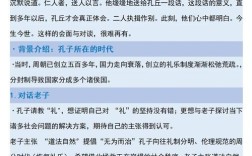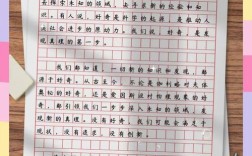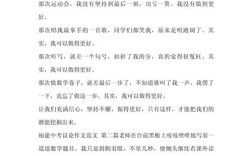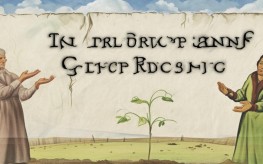于“模糊”处,见天地之大
当世界的轮廓被信息时代的洪流冲刷得愈发清晰,当高清摄像头能捕捉到万里之外的一抹微笑,当搜索引擎能瞬间给出任何问题的标准答案,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“去模糊化”的时代,我们追求精确,迷恋确定,将一切混沌与未知视为需要被扫除的障碍,我却认为,真正的智慧与境界,恰恰蕴藏于那看似混沌、不确定的“模糊”之中,于“模糊”处,我们方能见天地之大,品人生之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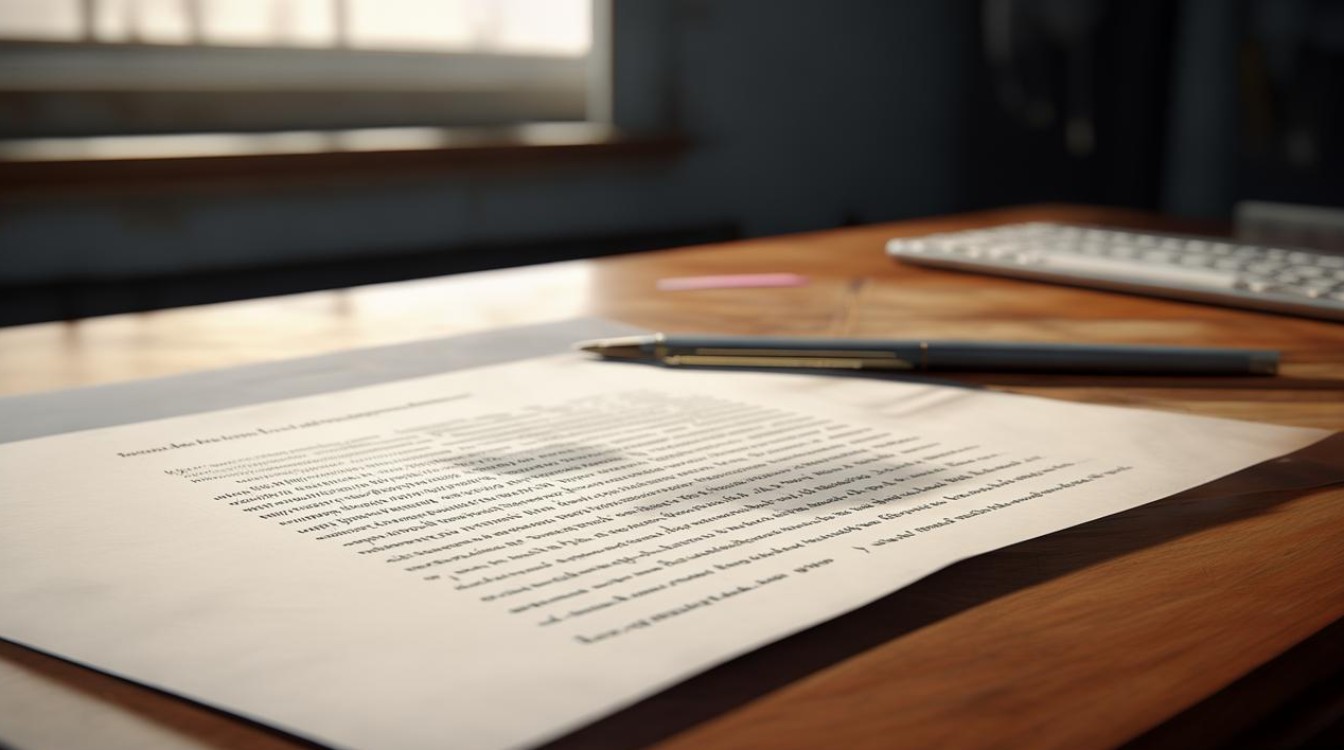
“模糊”是哲学的留白,是思想的疆域。
古希腊哲人芝诺曾说:“知识就像一个圆圈,圈内是已知,圈外是未知,圆圈越大,其接触的未知便越多。”这圈与圈的边界,便是一种“模糊”,它不是知识的贫乏,而是思想得以延伸的疆域,倘若凡事都用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去界定,世界将失去其丰富的层次与可能性,正是道德伦理中“灰色地带”的模糊,才引发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深刻思辨与文明进步,法律条文无法穷尽所有案例,才需要法官运用自由心证进行价值判断;科学理论无法解释所有现象,才为后继者留下了探索的广阔空间,正如中国画中的“留白”,那片不着笔墨的“模糊”,反而给予了观者无限的想象,使画作意境深远,哲学的魅力,不在于给出唯一的答案,而在于在“模糊”的边界上,激发我们永不停歇的追问与求索。
“模糊”是生活的智慧,是人际的温度。
生活中,我们渴望绝对的坦诚,却常常忽略了“模糊”所蕴含的温情与体谅,一句“没关系”可以化解无数尴尬的争吵,一个“我很好”的回答能抚慰远方亲友的担忧,这种“模糊”,不是虚伪,而是一种善良的“钝感力”,它为人际关系留出了缓冲地带,避免了言语的刀剑将彼此刺得遍体鳞伤,正如看一幅印象派的画作,你不必去计较每一笔的精准位置,而是感受其整体所传达的朦胧光影与情绪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亦如是,我们不必事事都刨根问底,给彼此一些空间和信任,关系反而会更加圆融与长久,刻意追求绝对的清晰,有时只会让生活变得尖锐而冰冷,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“模糊”,是一种洞察人性的智慧,更是对生活最温柔的接纳。
“模糊”是艺术的真谛,是审美的极致。
如果说精确是科学的语言,那么模糊便是艺术的灵魂,诗歌的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,靠的是意象的朦胧与情感的含蓄;音乐的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,利用的是音符间的停顿与留白;文学的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源于人物性格与命运解读的开放性,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,从不试图将一切和盘托出,而是通过“模糊”的笔触,邀请观者、听众、读者走进作品,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填补那片空白,从而完成一次独一无二的精神共鸣,这种“模糊”不是晦涩难懂,而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引导,它激发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创造力与共情力,让我们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之美。
拥抱“模糊”并非放弃原则,陷入虚无。
我们推崇“模糊”,是反对僵化的思维,而非无底线的纵容,在关乎真理、道义与底线的问题上,我们必须旗帜鲜明,毫不含糊,科学探索需要严谨的逻辑,社会运行需要明确的规则,个人成长需要坚定的目标,这里的“模糊”,是建立在一定认知基础上的弹性与包容,是智慧的表现;而“虚无”则是源于无知与怯懦的放弃,是思想的懒惰,真正的成熟,是在黑白分明处坚守立场,在混沌模糊处保持开放与弹性,懂得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自由切换。
在这个追求极致清晰的时代,我们或许需要为“模糊”正名,它是哲学的疆界,是生活的智慧,是艺术的源泉,它教会我们敬畏未知,体谅他人,欣赏不完美,学会与“模糊”共处,便是学会与这个世界温柔和解,与自己的内心和谐共生,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画布上,既有精准勾勒的轮廓,亦有挥洒自如的留白,于那片“模糊”之中,看见一个更辽阔、更深刻、也更可爱的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