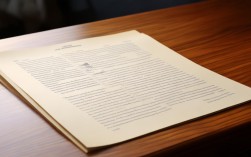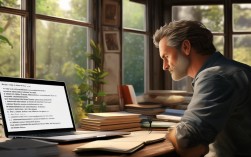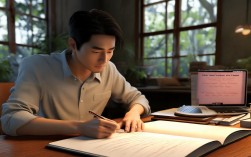人不以善言为贤
在人际交往与社会评价中,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现象:一些人能言善辩,谈吐不凡,言辞间充满了智慧与魅力,令人如沐春风,心生敬佩,我们便容易将“善言”与“贤能”划上等号,认为口才出众者必是德才兼备的贤者,历史的镜鉴与现实的体悟告诉我们,真正的贤能,并非取决于其言辞的华丽,而在于其行为的笃实、品德的醇厚与内心的真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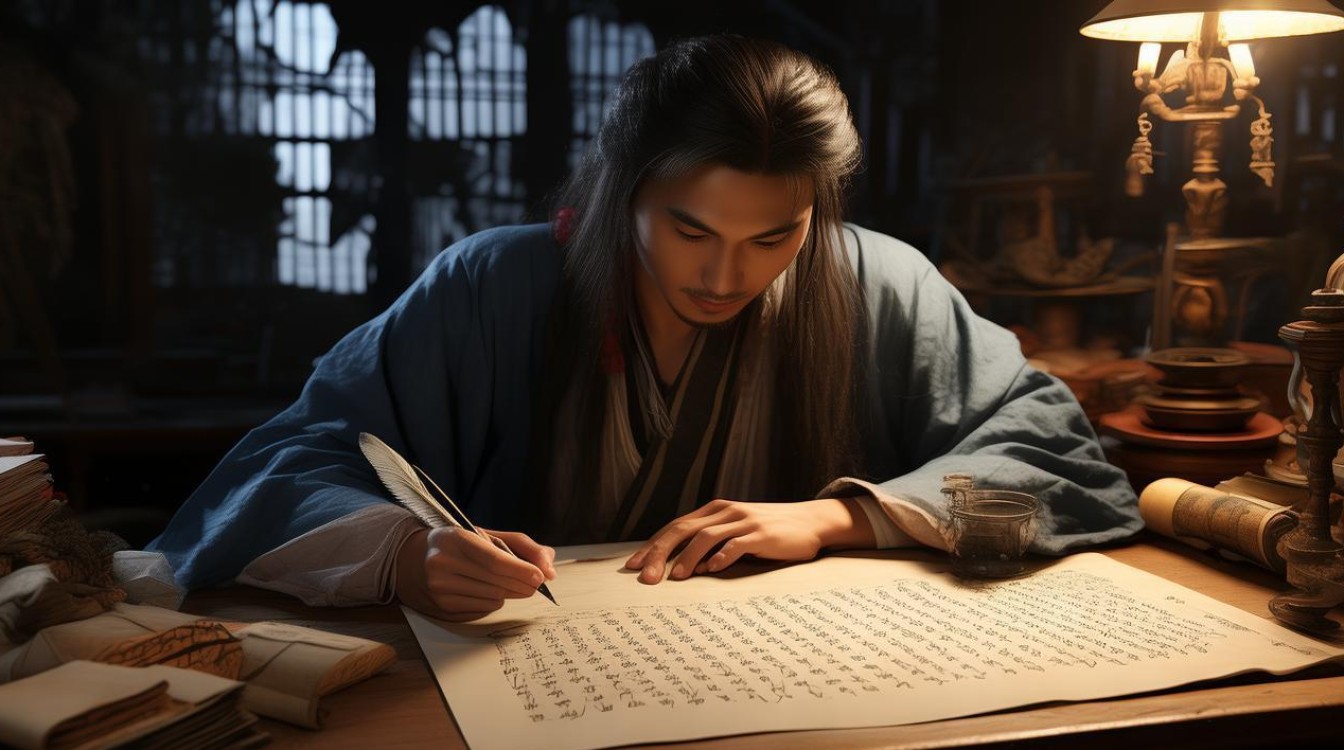
善言,是表象的锦缎,而非内里的基石。 言辞,如同一个人的衣冠,固然可以修饰其形象,传递其思想,但它终究是外在的、易于包装的,战国时期的纵横家,如苏秦、张仪,其口才可谓冠绝天下,一言可以兴邦,一言亦可丧邦,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,在列国之间翻云覆雨,影响了历史的走向,若以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贤者标准衡量,他们更多是“术”的运用者,而非“道”的践行者,他们的言辞服务于个人功业与政治利益,其动机未必纯正,其品格也未必高尚,可见,善言可以作为一种工具,既可以用来行善,也可以用来作恶,其本身并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根本依据。
贤能,是行为的金石,而非言辞的浮沫。 《论语》有云: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 孔子所推崇的君子,恰恰是那些言语谨慎、行动敏捷的人,贤者的价值,不在于他如何说,而在于他如何做,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言辞恳切,情真意切,其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誓言感人肺腑,但这番“善言”之所以千古传颂,并非因其辞藻华丽,而是因为它背后是他“亲贤臣,远小人”的治国实践,是“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”的艰难征伐,是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”的忠勇担当,他的贤能,是用生命和功绩写就的,而非仅凭笔墨言辞所能证明,反观当下,某些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,他们善于包装自己,言辞中充满了对理想、对情怀的宏大叙事,行动上却处处计较个人得失,其言与行的巨大反差,恰恰暴露了“善言”背后的虚伪与空洞。
察人,当观其行,更要听其心。 辨别一个人是否贤能,我们需要超越语言的迷雾,深入其行为的内核与品德的本质,战国时期的赵括,熟读兵书,谈起兵法头头是道,连其父赵奢都难以驳倒,可谓“善言”的典范,当他长平之战真正执掌帅印时,却因纸上谈兵、刚愎自用,导致四十万赵军被坑杀,赵国元气大伤,这个“纸上谈兵”的典故,深刻地警示我们:脱离了实践检验的言辞,不过是空中楼阁,真正的贤者,其言语是其内心品德的自然流露,是其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下来的智慧结晶,他们的言与行是高度统一的,所谓“言为心声,行为心迹”,评价一个人,不仅要听他说了什么,更要看他做了什么;不仅要看他如何对待他人,更要看他如何面对利益与诱惑;不仅要看他顺境时的豪言壮语,更要看他逆境时的坚守与担当。
诚然,我们并非全然否定言辞的重要性,清晰、准确、真诚的表达是沟通协作的基础,是传递思想、凝聚共识的必要手段,一个贤能的人,也必然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,但我们强调的是,言辞应为德行与能力的附丽,而非评判其本身的核心标准。 将“善言”等同于“贤能”,是一种浅薄的认知,容易被表面的华彩所蒙蔽,从而错失那些不善言辞却默默奉献的实干家,甚至可能被那些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所欺骗。
贤能的标准,从来不是一张能言善辩的嘴,而是一颗赤诚坚毅的心,一双勤劳实干的手,一系列经得起考验的功绩,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,我们应培养“听其言,观其行,察其心”的智慧,将目光从语言的表象投向行为的实质,从言辞的喧嚣回归品德的静默,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拨开迷雾,真正识别出那些沉默的脊梁与无言的丰碑,因为他们,才是社会真正的栋梁与贤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