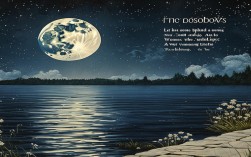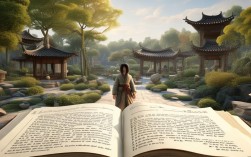命运的舵盘,终究握在自己手中
自古以来,“命运”二字如同一片深邃的星云,笼罩在人类文明的上空,引得无数哲人、先贤乃至凡夫俗子为之沉思、探寻与慨叹,它究竟是冥冥之中早已写就的剧本,还是我们用汗水与抉择一笔一划绘制的蓝图?面对这永恒的叩问,答案或许并非非黑即白,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命运,以及我们选择如何与它共舞。

我们必须承认,命运有其不可抗拒的“剧本底色”。 人生于世,无法选择的出身、时代、家庭环境,乃至某些天生的禀赋与偶然的际遇,都构成了我们命运的“底色”,正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,无法决定自己降生在和平的盛世还是动荡的年代,也无法预知明天与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,这些客观的、先在的条件,如同航船的初始位置与海上的风向,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航程,承认这一点,并非是消极的宿命论,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,它教会我们谦卑,让我们明白个体的力量在宏大的宇宙与历史长河中何其渺小;它也教会我们接纳,接纳生命中那些无法改变的缺憾与苦难,从而在逆境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解,倘若无视这一点,盲目地高喊“人定胜天”,则可能陷入不切实际的狂妄与无尽的挫败感之中。
命运的“剧本”并非一成不变的刻板文字,它留出了供我们挥洒的广阔“留白”。 如果说底色是命运的“必然”,那么我们的选择、努力与奋斗,便是命运的“偶然”,是真正塑造人生走向的关键力量,古希腊悲剧英雄俄狄浦斯,即便竭力逃避“弑父娶母”的神谕,却最终一步步走向那个早已注定的结局,这看似是宿命的强大,但换个角度看,恰恰是他每一次“选择”的结果——离开养父母、解答斯芬克斯之谜、登上忒拜王座——这些主动的行为,才最终将神谕变为现实,这恰恰证明了,命运并非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,而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过程,我们或许无法决定起点,但我们可以决定奔跑的方向与姿态;我们或许无法规避所有的风雨,但我们可以选择是撑起雨伞,还是淋雨前行,正是这无数个“选择”的瞬间,如同无数个交汇的岔路口,最终将我们引向截然不同的人生终点。
命运的真正奥秘,在于“既定条件”与“主观能动性”之间的辩证统一。 它既不是完全由外力操控的木偶,也不是天马行空的独断独行,一个真正成熟的人,懂得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,他既能坦然接受生命中的“不可控”,将挫折视为磨砺,将苦难视为修行;又能勇敢地掌控自己能掌控的部分,用知识武装头脑,用毅力克服困难,用善良温暖世界,这便是苏格拉底所说的“认识你自己”——了解自己的局限,也发掘自己的潜能;这便是尼采所倡导的“爱你的命运”——不仅接受生命中发生的一切,更要从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与意义。
回望历史长河,那些被我们铭记的伟大灵魂,无一不是在命运的浪潮中展现出非凡的驾驭能力,司马迁身受宫刑之辱,却能在命运的泥淖中奋起,著成“史家之绝唱”;贝多芬双耳失聪,却能在无声的世界里扼住命运的咽喉,奏响雄浑的《命运交响曲》;史蒂芬·霍金被禁锢在轮椅之上,却能用思想的翅膀,探索宇宙的终极奥秘,他们的人生轨迹,恰恰印证了:命运可以设置障碍,但无法剥夺我们选择如何面对障碍的自由;命运可以定义我们的遭遇,但无法定义我们遭遇之后的精神高度。
命运并非一道等待揭晓的谜题,而是一场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的修行,它是一张既有草图又留有白纸的画卷,我们既是画中人,也是执笔者,我们无法选择画布的材质,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何种色彩、何种笔触去描绘,决定我们人生价值的,不是命运给予了我们什么,而是我们如何回应命运的给予。
不必为前路的未知而惶恐,亦不必为过往的既定而懊恼,请相信,那看似遥不可及的命运星空,正由我们每一次的抬头仰望与奋力前行而变得更加璀璨,命运的舵盘,终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